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医药研发界的发明大王,人称“医药爱迪生”(The Edison of Medicine)

Bob Langer教授(Credit: Tony Luong)
编制按:
我们对麻省理工学院的Bob Langer教授充满了敬意,看到这篇报道文章时爱不释手,由衷希望将它翻译成中文,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分享精华,向Langer教授学习科研、管理、创新。本文为编译作品,偏颇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老师/朋友们批评指正!衷心感谢!

前言

这是2016年的一个上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美丽而繁忙的麻省理工学院,享誉世界的MIT。这座著名的高等学府的校园里人来人往,学生们奔向各自的教室、实验室,开始了又一个充实的一天。James Dahlman(詹姆斯·达尔曼)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Koch癌症综合研究所,走进Bob Langer(鲍勃 兰格)教授的办公室。他是来和自己的博士导师,Bob Langer和Dan Anderson,道别的。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即将离开美丽的MIT校园,加入佐治亚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开始他人生中第一个教学职位。职业生涯扬帆启航之际,他希望得到两位导师的指导。

“少年立志当驽云!大丈夫,立大志,做大事!” 兰格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深情地说到。“做一些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的大事,而不是渐进的修修补补的小事。”
这不仅仅是一位老师鼓励自己的毕业学生的励志名言,更是指导教授本人度过四十年职业生涯的座右铭。兰格教授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化学工程师,是控释药物传递系统和组织工程领域的先驱。这些箴言是宝典秘笈,帮助他的实验室成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研究机构之一。
的确,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还是政府实验室,任何一位领导不同领域高素质人才组成的团队的人都可以从Langer模式中学到很多精华。兰格教授以五管齐下的方式加快发现转化的速度,确保将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孵育,在现实世界诞生,成为一件有价值的产品。Langer模式包括:
(1)聚焦具有高影响力的创意;
(2)跨越研究与商业开发之间的“死亡谷”的流程;
(3)促进多学科协作的方法;
(4)使研究人员持续流失以及有限的项目资金和周期成为加分项;
(5)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提供全力支持的领导风格。
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Kent H. Bowen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学术实验室和企业实验室。他说,美国每年花费大约5000亿美元用于研究,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平庸的,如果有更多的高度协作的实验室,像兰格实验室那样专注于高影响力的研究,美国将实现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
兰格教授在多个方面成就非凡。他的H指数得分230,是全世界所有工程师中最高的。H指数得分是衡量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以及被引用的频率。兰格教授已有1,100多个已获批和审评中的专利,已被许可或再次许可给大约300家制药、化学、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他因此而获得了“医药爱迪生”(The Edison of Medicine)的尊称。他的实验室以独立或合作的方式创办了多达40家公司,除了其中一个之外,其余的39家公司都作为独立实体或作为收购公司的一部分而正常运营。汇总起来,这些公司的估计市值超过了23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Living Proof,一家头发产品公司,联合利华正在收购,交易金额未公开。
实验室的终极“产品”是人才:大约9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从这里获得研究生学位或开展博士后工作。他们其中几十位已经在学术界、企业界和风险投资界做得如火如荼,非常的成功。十四个已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十二名进入美国国家医学院。
多学科合作途径在学术界非常流行,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在提高马力,这反映了大学对解决现实问题和产生新业务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认识到这样做往往需要多种多样的专业知识。尽管长期以来这在商业世界中一直很常见,公司也可以通过应用兰格教授的从研究到产品的流程的精髓来进一步改善结果,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产品,一次次刷新或重塑企业。

兰格教授在其MIT办公室中
聚焦具有高影响力的创意
选择项目时,兰格教授的标准之一是考虑对社会的潜在影响,而不是资金。初衷就是:如果你创造出一个带来重大变化的东西,那么客户和钱就会随之到来。这与许多大公司的做法有着深刻的差距。如果一个产品的想法是如此全新,那么无法计算其打折现金流,这些公司往往不会追求,或者当研究遇到障碍时就放弃,雄心勃勃的研究几乎总是这样。
对兰格教授来说,“影响力”是指发明人可以帮助到的人数。据风险投资公司Polaris Partners估计,从兰格实验室出来的生命科学企业有可能影响近47亿人的生活。Polaris Partners投了其中很多的公司。例如,可以植入大脑的晶片是1996年上市的实验室产品,将化疗药物直接递送到胶质母细胞瘤所在的位置。另一款产品最近被转给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新公司Sigilon,是与其它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发的1型糖尿病的潜在治疗方法。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将β细胞用高分子包裹起来可以保护它们躲避人体的免疫系统,但依然可以检测血糖水平,释放适量的胰岛素。
果然如预期的那样,这些扎扎实实、雄心勃勃的项目吸引客户接踵而至:基金会、公司、其它实验室以及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内的政府机构。基金会和公司目前资助实验室1730万美元年度预算的63%,从比尔盖茨基金会、前列腺癌基金会到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罗氏(Hoffmann-La Roche)。盖茨基金会综合开发与疟疾总监兼基金会与实验室的首席联络官丹·哈特曼(Dan Hartman)表示:“我们决定与鲍勃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实验室在药物控制传递方面的成功记录。鲍勃和他的团队的创造力和技术专长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项目选择的第二个标准适合实验室的核心领域:药物传递、药物开发、组织工程和生物材料。“我们所做的大部分项目都跨界,跨越材料学、生物学和医学。” 兰格教授介绍说。
第三,通过应用或扩大现有科学来征服医疗挑战和科学挑战,无论是他的实验室独立完成,还是与他人合作。
这种方法与关于从研究到产品的过程的长期盛行的观点相左,那些观点认为它是线性的,正如:基础研究(旨在扩大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不考虑实际应用)通向应用研究或转化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进而导致商业开发(将发现转化为实际过程和产品),所有这些以放大直至大规模生产而告终。这个范例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兼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Vannevar Bush,他也是政府坚决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
二战以来,大学进行了基础研究的绝大部分,但企业也参与其中,比如:AT&T、康宁、杜邦和IBM。最近几十年来,大公司已经认为它太昂贵,风险太大,成果获得缓慢而且不可预知,捕捉价值可能很困难。所以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学术界,有时候购买发现项目或获得许可,或投资、收购开发这些产品的初创企业,其它时候则资助学术研究或让他们的科学家在学术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然而,线性范式从来不是普遍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伟大的研究人员推动了基础科学的前沿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普林斯顿政治科学家Donald E. Stokes为他们工作的空间创造了一个术语:巴斯德象限,强调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追求对微生物学的基本了解以抵抗疾病和食物腐烂的努力。其它例子包括贝尔实验室,其科学家在改进和扩展通信系统的同时获得了基础性发现,以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创新机构之一。
兰格实验室也在巴斯德象限之中。尽管研究人员将大部分努力用于可以解决关键问题的应用科学和工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推动基础科学的边界。例如,兰格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通过多孔聚合物在几年内以指定剂量和次数在体内释放大分子药物的一种方法。这涉及跨越物理和数学的一个交叉领域,称为渗透理论。
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比如康宁在量子通信和捕获二氧化碳的材料方面所做的努力、IBM在认知计算和智能城市中的努力、Alphabet在医疗保健和自动驾驶的汽车的努力,公司并不努力将早期研究与主要的实际应用相连接。哈佛商学院教授Gary P. Pisano说:“如果你解决一些社会的大问题,你实际上会赚很多钱。”
Koch研究所神经科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Susan Hockfield同意这个观点。她说:对于企业研发的状况有很多的关切和怀疑。例如,制药企业在很早的阶段投资大量的探索性研究。如果与非工业界的生物学家和工程师更有效地合作,他们能不能做得更好吗? 我刚刚完成了审查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委员会工作,我很惊讶于他们的辉煌的想法和高质量的研究,但他们可以把更多的发现转化为上市产品吗?

兰格实验室的休息室里的公告栏
跨越研究与商业开发之间的“死亡谷”的流程
当然,选择正确的项目只是第一步。实现的道路可以是漫长的,沟壑纵横。兰格教授有一个公式,帮助发现项目成功通过早期研究和商业开发之间的死亡谷。
关注具备多种应用的平台技术
许多企业和学术实验室都希望能够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必考虑超越这些问题。兰格实验室则拥有更广阔的视野。Polaris的创始合伙人Terry McGuire表示,除了创造更广泛的市场之外,这一战略还允许公司追求无法预料的应用。例如,Momenta,2001年推出的一家开发新的方法来理解和调整糖分子结构的公司,最初开始对肝素进行测序以治疗癌症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等疾病。然而,它后来意识到,它也可以利用新兴技术来测定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现成药物Lovenox的复杂结构。这项工作产生了一种用于预防和治疗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生物仿制药,第一年就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
虽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经常有一种用途成竹在胸,有时他们也设想了各种应用。例如,兰格产生了可植入微芯片的想法,该芯片可以多年释放药物,并可以在半导体上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在体外轻松控制。他想象,芯片不仅可以用来运送药物,还可以放入电视机中释放可以增强观看体验的气味。
获得广泛的专利
麻省理工学院一直是学术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先锋。但是兰格教授在追求特别强大的专利方面尤其独树一帜。他的目标是限制,有时甚至是阻止,其他人声称对某个领域的权利,以便这些公司愿意为IP付费,支付将发现进行商业化所需的资金,这种投资通常必须支撑昂贵的临床试验,大大超过了研究阶段的费用。兰格教授的一些秘密有:使用伟大的律师,让他们挑战彼此的建议;消除可能限制索赔的不必要的字眼;清楚地描述所有条款和支持性实验测试,以防止专利诉讼中的歧义。
在著名杂志上发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
在《自然》或《科学》等著名杂志上亮相可以验证科学发现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同时广而告之,面向的不仅仅有其他学者,也有潜在的商业投资者。
在动物研究中证明概念,不要将发现过快地从实验室推出。原因有两个方面:提高发现成功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商业化遇挫的机会。这些在大学甚至企业界都是普遍存在的坑。
最近的例子是使用超声波直接向胃肠道快速递送多种类别的药物,包括小分子、大分子生物制剂和核酸,先前必须注射这些药物。尽管早期的成果初现希望,实验室科学家急于启动一家公司将这一发现商业化,兰格教授拒绝了。他希望保持实验室团队的完整性并继续从事技术研究,例如,通过对大型动物进行慢性治疗研究以展示其安全性,并开发新的配方进一步加强药物的递送。
这种额外的研究不受商业时间表的束缚,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实验室证明该技术可以递送全新的一类药物(不用装入胶囊的核酸),从而扩大其潜在的应用范围。该小组还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了更多关于该研究的文章,证明了原始数据是可靠的和可复制的。只有此时,兰格教授才同意帮助新公司Suono Bio筹集资金,该公司接管下一步的开发工作。
奖励研究人员
麻省理工学院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发明专利使用费收入的三分之一奖励发明者,其余的归研究人员所在的部门或中心、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许可办公室和大学的普通基金。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制定了类似的政策,但这种方法在企业界仍然是非常不寻常的。

让研究人员参与商业开发
多年来,许多成员离开实验室到接受项目的公司就职,在那里,他们对将技术转化上市的热情已经与专业技术一样重要。兰格教授介绍说:“很多公司做得很好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学生加盟成为其主力。他们真心相信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的研究,并希望使其成为现实。” 其他研究人员留在实验室或转到其它大学之后作为顾问为这些公司出谋划策。兰格教授自己出任波士顿地区的十家初创企业的董事会,这些公司都是基于他的研究而成立的。虽然越来越多的大学放宽了对教授参与商业活动的限制,甚至通过启动孵化器和加速器来鼓励商业化,但是在许多缺乏麻省理工学院成熟的创业文化的地方,人们仍然对这种活动感到不安。而在企业界,科学家们深入参与商业化是非常不寻常的。
许可都以使用该技术为前提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使用它从兰格实验室许可到的技术,Langer实验室可以要求公司放弃许可。用于治疗脑肿瘤的晶片就是一个例子。授权引进该技术的公司被另一家公司购买,而后者对该治疗技术不感兴趣。麻省理工学院与之接洽,使得它同意启动一家初创公司来开发晶片,回报是较低的许可费用。很少有大学或公司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积极地管理他们的专利。因此,他们的许多潜在的有价值的发现未被利用。
促进多学科协作的方法
兰格实验室的一个团队研究口服药物输送装置,该装置可以在胃中逐渐释放药物数周或数月。团队提出了一个星形设计,后来,一个具有建模经验的机械工程师加入了这项工作并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团队选择了一个星形?为什么不是其它形状? 该团队评估了几种可能性,包括六边形和各种星形,发现六角星最适合胶囊,在胃中停留的能力方面表现最佳。新的团队成员还提出了关于臂和中心的刚度、界面处弹性体的强度以及展开装置的尺寸的考虑。这些讨论转换为可使设备持续更长时间的材料。
哈佛大学胃肠病学家、生物医学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机构负责人Giovanni Traverso表示:“这正是当您将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会发生的事情,这激发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思考方式。” 兰格实验室的团队包括化学、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分子生物学家、医务人员、兽医、材料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制药化学家。来自不同学科的会员在Koch研究所六楼的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并肩工作。
多学科实验室正在萌芽,因为学术界认识到他们在应对从癌症与全球变暖等方方面面挑战的价值。但这场革命还处于早期阶段。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报告“融合:健康的未来”由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联合撰写,强调了将工程、物理、计算、数学和生物医学等科学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帮助解决世界上许多巨大的挑战。它呼唤教育、工业、政府方面的雄心勃勃的改革,包括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中形成“融合文化”以及政府资助研究这一实践的变化。
兰格的声誉、他的实验室所面临的挑战、提供的就业机会,包括参与初创企业的机会,吸引了大量的申请人。实验室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19名研究人员,外加每学期30至40名本科生。Langer实验室每年开放10到20个博士后职位,收到的申请数目高达4000到5,000个。兰格实验室在特定项目需要专门技能的时候全球搜索人才。
申请人必须具有优秀的学历和积极性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兰格教授、Traverso、生物医学工程师和MIT科学家Ana Jaklenec组成的领导团队寻找可与他人相处,擅长沟通的优秀人才,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向同事解释他们的领域,并设计所有人都可以重复的实验。在MIT掌舵八年的霍克菲尔德说:技术语言、工作实践、价值观甚至是定义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差异成为多学科实验室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
Jaklenec展示了一个充满方程式的白板。这来自两个博士后的会议。两位博士后中一位是生物学家,另一位是生物医学工程师,他们正在合作开发单次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该疫苗可以停留在身体内并随时间释放。生物学家在探索降解病毒菌株的机制,而生物医学工程师则致力于解决热稳定性问题。两个人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数据集放在一起时说不通。事实证明,他们使用不同浓度的疫苗进行实验:工程师使用的是临床试验样品,而生物学家则是按照她的领域的分析方法所要求的。研究人员们必须调整他们的实验以便比较结果。这些问题并不罕见。Traverso说:“挑战正是让人们说同样的语言,并且认识到某些事情上没有单一的专家。”
即使没有明显的需要或契合,兰格教授经常会引进一些行业大咖,他们有着不寻常的声誉。他说:“你依靠人才来碰运气。Gio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Traverso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癌症生物学家Bert Vogelstein教授那里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涉及早期检测结肠癌的新型分子检测。当他联系兰格教授时,他正在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和妇女医院完成一个内科住院医生实习,试图找出如何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使用他得到的胃肠病学奖学金。他告诉兰格教授虽然他有兴趣开发在胃肠道输送药物的系统,但他并不是工程师。兰格教授还是聘用了他。这笔下注得到了很好的回报。Traverso展示了通过胃肠道装置递送药物的几种不同方法的概念。盖茨基金会认为这项工作可能会解决贫困国家想要解决的问题,于是提供了大笔资金。Novo Nordisk(开发注射微针),Charles Stark Draper Lab(开发新的可摄入系统)和Hoffmann-La Roche(开发一类新药物的递送系统)的资金也纷纷到来。
使研究人员持续流失以及有限的项目资金和周期成为加分项
像所有的学术实验室一样,兰格教授看到人员不断的加入或离开。博士生通常停留四至五年,博士后二至三年,本科生最少一个学期,最多四年。新来的人都为了未来而受到训练,人们可在他们产出的高峰期离开。令大多数人头疼的问题被以新鲜的眼光看待,兰格教授和许多同事认为人员流动有着许多超过缺点的积极因素,称这个问题为“持续不断的刺激”。流失率是可精确预测的,与项目的长度相关。庞大的基金都是结构化的,使得实验室可以逐步扩大。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有限任期以及基金明确的期限(通常为三到五年,根据是否达标而决定是否延续)成为实在的压力,迫使研究人员努力去获得好结果。
“学术研究实验室模式已经遭到大量的讥讽。我们被告知这是低效率的,” 霍克菲尔德说。“但它是辉煌的。汇集来自不同年代的和具有不同层次经验的人们,这太棒了。教师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解,了解文献和历史。学生和博士后有很多精力、雄心和疯狂的想法。教师指导学生,为那些疯狂的想法提供表达的渠道。本科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他们心目中万事皆有可能。”
时间有限、高度积极性的超级明星队伍、成功的科学家领导、需要获得积极结果的强大压力,这听起来像DARPA公式,证明该模式的应用远远超出学术界。

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提供全力支持的领导风格
鳕鱼角的一个下雨天里,兰格教授和他的妻子劳拉谈到他的实验室管理与常规的实验室的不同之处。拥有MIT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劳拉表示:“与其它实验室的研究生讨论时,他们经常将他们的导师形容为控制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验室是导师们的宝贝。他们想管理研究的每一部分。他们很难让他们的学生探索、犯错误。但是,不给人们自己搞明白的空间,可以扼杀他们的积极性,或训练他们不要冒潜在的创新风险。”
兰格教授点头赞同。在他的领导下,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提供关于项目的金点子,选择自己愿意从事的项目。“这是团队的努力,” 他说。“赋予人以能力。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很受重视,可以畅所欲言。” 这与大多数学术实验室和公司实验室形成对比,在那里主管选择项目。
当前的和以前的实验室成员分享说,兰格教授让人们看到可能性,让他们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医学科学教授Gordana Vunjak-Novakovic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兰格实验室工作,表示她对兰格模式心领神会,在以同样的方式运行自己的40人的实验室:“我从来没有告诉人们要做什么,而是帮助他们看到可能性,让他们真正对其中一个感到兴奋,让他们为自己的想法开展工作。” 许多兰格实验室的博士后和研究科学家,还有一些博士生,有机会同时开展多个项目。
兰格教授安排Jaklenec和Traverso作为联合首席研究员,这是另一个偏离了常规的做法。权力在整个实验室里根据人们的想法、主动性以及他们的研究吸引到的资金而被分配。兰格教授在启动阶段给研究人员,特别是研究生,很多的指导,以确保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项目得到最佳的安排。他还帮助决出谋划策。比如,开发长期保持在胃中的药物传递装置的项目开始时,他和Traverso决定探索两种可能性:一种漂浮在胃里,一种附着在胃壁上。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后,他们选择继续研究浮动这一选项,并找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后兰格教授基本上退出。“那以后,我不告诉人们该怎么做,” 兰格教授说。“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到研究生院,你是以你回答别人问题的好坏来被判断的。你被给予一个考试成绩。但是,如果你想想你在生活中被判断的方式,不是你的答案有多好,而是你的问题有多好。我想帮助人们从提供良好的答案转变到提出好的问题。”
Gary Pisano认为这一理念是实验室成功的关键。他解释说:一般趋势是我要告诉你该怎么做,这样你可以做得更好,实验室会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在兰格实验室里这样做,你会把实验室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人们会说,“好的,鲍勃,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兰格教授不想要那种实验室。他的实验室是人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实验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为商业界伟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的原因。
与此同时,兰格教授确保研究人员知道如果遇到麻烦,他们可以依靠他和他朋友圈里的资源。丹麦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艾米·汉密尔顿(Aimee L. Hamilton)研究过兰格实验室,他称之为“指导下的自治”。兰格教授的反应令人称奇,他的iPad似乎粘在身上,他用几分钟迅速地回答电子邮件。康涅狄格大学教授Cato T. Laurencin在20世纪80年代从兰格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他回忆说,他曾经拨打兰格教授的手机号码,问了关于兰格写的一篇文章的一个问题。兰格教授十分钟后就从芬兰打了回来。
兰格教授也以他的方式帮助离开实验室的组员们获得好工作,他与数百名实验室校友保持联系,如果有需要则迅速提供帮助。在欢送詹姆斯·达尔曼的告别会议上,他提出帮助审阅达尔曼的基金申请。兰格教授也与他网络中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他以朋友称呼许多资助他的初创公司的风险投资家,包括Polaris的Terry McGuire、Flagship的Noubar Afeyan、Third Rock的Mark Levin。兰格教授、McGuire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去年在波尔多度假,兰格的女儿参加McGuire女儿的婚礼。
兰格教授在人脉网络方面的投入收到了很好的回报,包括收获颇丰的研究合作,出色的学生被推荐给实验室,为初创企业提供人才,等等。兰格教授不仅为实验室成员启动初创企业铺路,而且需求一旦出现,他也动用他的网络来帮助。来自兰格实验室的三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执行主席艾米·舒尔曼(Amy Schulman)回忆说:“鲍勃经常针对某个人都有一个好的想法。因为他知道很多机会,当人们考虑换工作时,人们常常会接触鲍勃。所以这成为良性循环。”

结论

当与兰格教授合作过的人谈论他时,人们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他是他的从研究到产品模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无法复制的辉煌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模式,包括他的“好好先生”的领导风格,不能被复制。如果每一家公司的实验室都像兰格实验室一样呢?如果他们在少数几个领域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客户难道不会带着最紧迫的问题来找他们吗?如果他们吸引超级明星研究人员,为他们提供机会来解决可能改变世界的问题呢?
Gary Pisano说:“也许公司可以建立一个最好的研究运营平台,让精英中的精英尝试在几年内做他们想做的大胆的事情,而不是花费30年担心下一次的升级。” 他的哈佛同事Willy Shih补充说,这样一种方法不仅可以让公司从事更多雄心勃勃的项目,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终止平庸或差劲的项目,人们在实验室的流动将会产生自然而然的后果,那就是无法经受住新鲜的考验的想法被停止。
兰格教授说:“我想解决可以改变世界的问题,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贯穿我倾尽毕生精力从事的科学。我帮助创办公司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延伸。我想看看我究竟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通过学习、利用兰格实验室的价值观和模式,一家公司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参考资料:
The Edison of Medicine (作者:Steven Prokesch,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图片来源:原文、MIT官网。版权归拥有者。
本文为编译文章。因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偏颇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衷心感谢!
—— 欢迎阅读近3个月内10,000+文章!——
-
它是当今一代名药,治愈了卡特总统,开创了重要的先河,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艰辛往事!
-
划时代!FDA批准全球第一款CAR-T疗法!
-
肿瘤免疫疗法最新进展之理论篇:PD-1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战狼2》中一箭封喉的毒素是什么?是否再次提醒我们一个新药研发的机会?
-
重磅 | 癌症,被重新定义!
-
10 : 0!完美数字!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热烈祝贺诺华在CAR-T领域代表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
FDA推荐的仿制药开发机会!长长的名单!药时代强烈建议中国药企仔细研究,积极跟进,把握这一大好商机!
-
写在父亲节:我曾经能给绝症父亲最好的药物
-
谢雨礼博士 | CFDA最近的改革及其影响
-
FDA新局长的三把火:每个仿制药要有三家制造商!
-
划时代!FDA今日加速批准首款不区分肿瘤来源的抗癌疗法
-
Nat Methods:给我换个美女实验员!
-
FDA新局长Gottlieb博士对全员的第一次讲话。精彩!感人!



欢迎联系我们!drugtimes@qq.com
发布者:药时代,转载请首先联系contact@drugtimes.cn获得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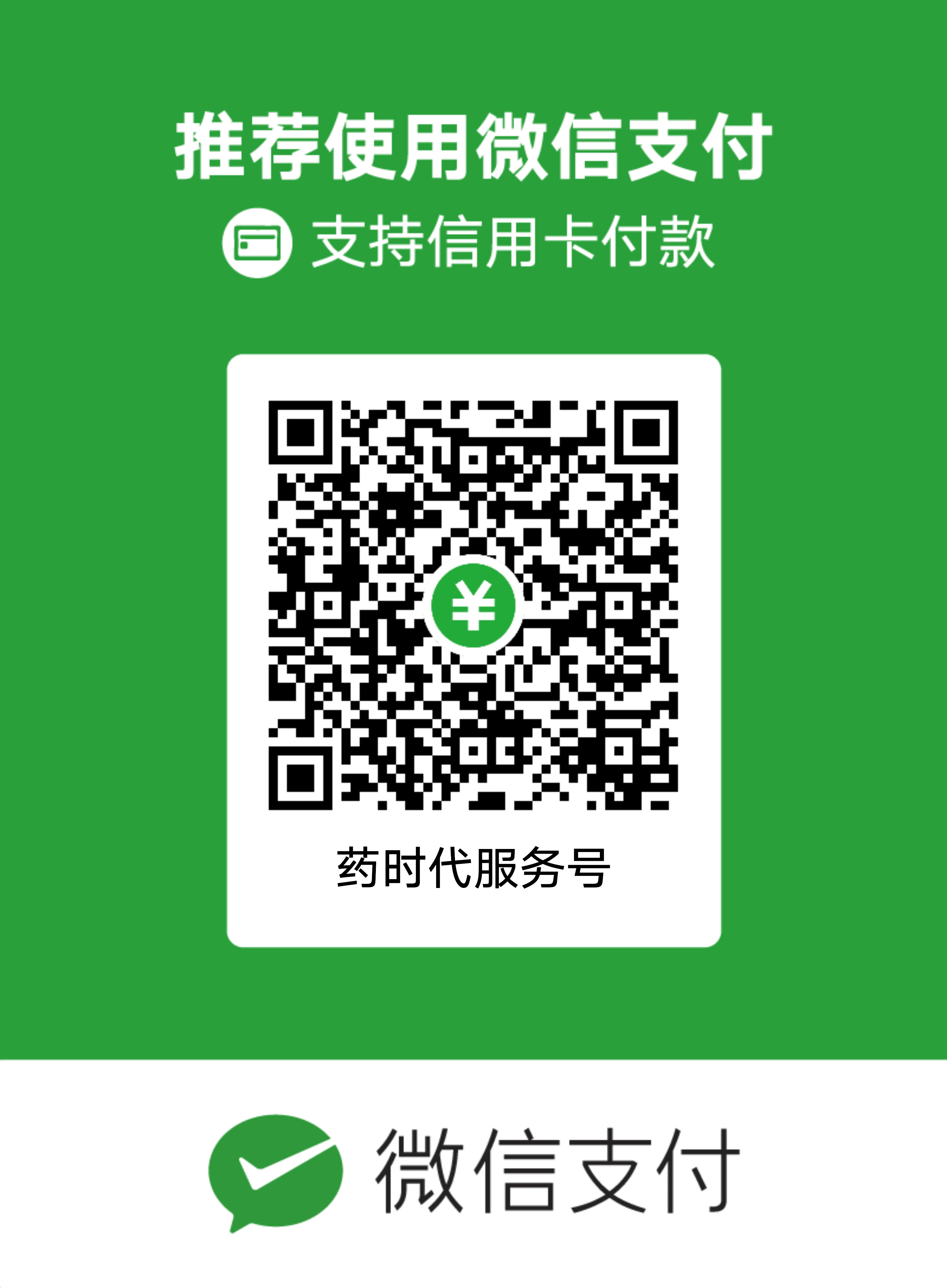 为好文打赏 支持药时代 共创新未来!
为好文打赏 支持药时代 共创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