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药时代):徐亦迅博士 | “诺光灯”下的科学史掠影(上)

预计阅读时间:22分钟
【药时代编者按】2019年11月9日,作者应邀在海外华人企业家联合会 (OCEAN) 20周年年会上做有关诺贝尔奖历史的科普报告。整个报告从新视角对四个案例进行了科学史分析:一个物理学奖,两个生理学奖,一个化学奖。本文是以原讲稿为基础,适当添加解说内容后改写而成。

1895年11月27日,炸药大王诺贝尔 (Alfred Nobel) 在去世前一年立下的遗嘱中写道:“ …… 我所留下的全部可变换为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这份资本由我的执行者投资于安全的证券方面,并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中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先生选择表彰的五个领域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人类和平,其中文学奖与和平奖比较容易按照类似电影奥斯卡奖的“前一年”范围来颁奖,但他显然低估了“时间的考验”对于客观评估自然科学成果的重要性。
今天首先谈一下1956年宇称不守恒现象的发现以及完成重要实验的吴健雄教授为何没被诺奖委员会所青睐。作为背景知识,我们需要介绍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镜像对称 (reflection symmetry)。

图一来源:Youtube科普视频;Gardner, M. (1990) The New Ambidextrous Universe, Chapter 1: Mirrors
很多人在照镜子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镜中上下没有颠倒,而左右是颠倒的?其实所谓的“左右颠倒”只是一个幻像,因为左和右这两个方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照镜者的视角有关。如果单纯从镜外人的视角来看,左右并没有颠倒,只有从镜中人的视角反过来看,我们才觉得镜中的虚像出现了左右互换。三维空间的直角坐标中真正发生颠倒的只有图一中代表前后方向的绿色箭头,正对一面平镜时的前后方向无疑在镜子是相反的。

图二:矢量叉积的右手定则
我们再回想一下三维矢量代数中定义两个矢量叉积的右手定则(图二),如果前后出现了反向,那么为了数学上的自洽,我们在镜中使用的其实是满足左手定则的直角坐标系。因此镜像中颠倒的并不是左右的方向,而是左手系和右手系这两个不同的三维直角坐标系发生了对换。
著名科普作家Martin Gardner在《The New Ambidextrous Universe》一书中还给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例子。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左右直角折叠的两面镜子(或者如图一显示呈左右弧线的弯镜),那么哪怕从镜外人的视角看,镜内和镜外的左右手都没有颠倒。而如果我们面对上下直角折叠的两面镜子(或者如图一显示呈上下弧线的弯镜),那么镜外人会惊讶地发现上下发生了颠倒。这可以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左右颠倒”和“上下不颠倒”都是人脑对眼中图像的再解释。
1956年,旅美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对困扰当时高能粒子物理学界的“奇异粒子”现象产生了兴趣。这一现象也被称为“θ-τ之谜”,θ介子和τ介子明明具有相同的质量和半衰期,它们的衰变方式却不一样:

杨李二人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想要判断θ和τ在本质上究竟是同一种还是不同的基本粒子,关键在于探究衰变这一弱相互作用现象是否也满足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宇称守恒定律 (镜像对称)。
宇称守恒定律认为镜外和镜内所观测到物理学规律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而大量实验也证明引力场,电磁场,以及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完全守恒。李杨二人在深入讨论时忽然意识到,到1956年为止,似乎还没有专门设计的实验用来验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是否守恒。为了确认可能存在的宇称不守恒能否从已有的β衰变实验结果中推论而出,他们花了几周的时间进行了大量周密的理论计算,发现这些结果和宇称是否守恒没有一点关系。
李杨二人在1956年6月投稿的这篇经典论文还有一个独到之处:他们在理论计算指出已有实验的局限性之后,还精心设计了两套新的弱相互作用实验方案,可以毫不含糊地验证宇称是否守恒。其中第一套方案的构思得益于两人与吴健雄教授的讨论,而吴教授在当时已是β衰变实验的权威学者之一。这个实验的关键是选用钴60这一放射性同位素,它是通过慢中子束轰击稳定同位素钴59而人工合成的:

很多人对钴(Cobalt)这个过渡金属元素的唯一印象恐怕来自中学时代背诵元素周期表时的那句“铁钴镍铜锌”。钴60的原子核由27个质子和33个中子构成,它的半衰期是5.27年,容易通过两步β衰变而转化为镍60并同时释放出一个电子,一个反中微子,和两种γ射线:

一个钴60样品每秒钟可以释放出上万个电子,因此是极好的放射源。我们知道质子和中子都有一种最早在电子研究中发现的内蕴角动量:自旋 (spin)。当有外加磁场时,量子化的自旋角动量就能通过磁矩这个物理量被实验者观测。对于宇称是否守恒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在概念上区分真矢量 (又名极矢量,polar vector或proper vector)与赝矢量 (又名轴矢量,axial vector或pseudovector),它们在镜像反射下具有截然不同的行为:

图三来源:黄亦斌, 聂义友 (2007) 镜像对称性在电磁学中的应用,《大学物理》, 10: 24-30.
图三的下半部显示,类似矢径这样的真矢量 (线速度,动量,电场强度,…),其镜像中与镜面M平行的分量不变,而与镜面垂直的分量反向 (参见图一中的绿色箭头);而图三的上半部显示,类似角速度这样的赝矢量 (角动量,磁场强度,…),其镜像中与镜面M垂直的分量不变,而与镜面平行的分量则反向。如果想在直觉上快速理解赝矢量在镜中的平行分量为何要反向,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图二中两个三维矢量的叉积。两个真矢量的叉积是一个赝矢量,而量子化的自旋角动量和经典力学中的角动量一样,都可视作是矢径与动量的叉积。对于一个叉积的镜像而言,镜外的右手定则到了镜内只有变成左手定则才能在数学和物理意义上自洽。左手和右手坐标系的不同导致了赝矢量与镜面平行的分量需要在镜中反向。

图四:自旋角动量的赝矢量特性与吴健雄等人的钴60原子核β衰变实验基本思路。
前文已经提到,钴60原子核在β衰变过程中会释放一个电子【注意:这并非来自核外电子层,而是原子核本身衰变的产物】,如果我们能用低温物理学手段使得钴60核沿着外磁场方向极化 (样品中所有钴60核的自旋角动量指向一个方向),那么通过互为镜像的两套实验装置来测量电子飞出的各向异性角度分布,就能验证宇称是否守恒 (图五)。

图五:吴健雄等人检验宇称是否守恒的钴60原子核β衰变实验设计与结果解读。
吴健雄深知这个实验将面临两大挑战:(1) β衰变的电子探测器在极低温的环境下如何保持功能正常?(2) 如何使一个非常薄的钴60核β放射源保持极化状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得到足量的统计数据?吴教授本人并非低温物理学专家,而她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低温物理设备水准又不够,于是决定和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国家标准局 (NIST) 科学家安伯勒 (Ernest Ambler) 联系合作事宜。
1956年9月,吴健雄作客NIST正式开始了与安伯勒等四位低温物理学专家合作的实验。虽然双方由于性格与做事方式的差异而并不愉快,但是整个实验在排除了种种困难之后到了圣诞节前后已接近成功,令人惊喜地看到了宇称不守恒的迹象。1957年1月4日的哥大物理系午餐聚会上,年轻的李政道并没有过分在意吴教授之前关于暂时不向外人透露的叮嘱,把实验接近成功的消息告诉了与会人士。在场的莱德曼教授 (Leon Lederman) 听后心想,如果弱相互作用下宇称真的不守恒,那么以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加速器实验,加上一点运气,也许就能利用π和µ介子来完成李杨论文中设计的第二套实验方案。在IBM就职的实验物理高手加文 (Richard Garwin) 及时提供了巧妙的设计思路,莱德曼团队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实验,结果清晰地指向宇称不守恒,可谓后发先至。
不过莱德曼颇有科研道德操守,论文写完后等了吴健雄团队一个星期,最后两篇论文在1957年1月15日同一天寄到《Physical Review》杂志,不久后又同一天发表。这在很多人看来,显然是两个实验小组几乎打平的格局。吴教授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介绍NIST四位合作者的贡献,导致安伯勒的老师柯提 (Nicholas Kurti) 专门发文表达不满。这些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导致吴教授没能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 (图六)。

图六来源:诺贝尔奖提名数据库中有关吴健雄被提名的完整记录
李杨二人首次被提名就在当年顺利获奖,而吴教授从1958年开始的几年内先后被提名7次,莱德曼教授从1959年开始获得提名,两人最后都没能因为证明宇称不守恒的实验而获奖。莱德曼后来以发明中微子束的实验方法而获得了1988年度的物理学奖。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我的推断是,倘若李杨需要等待一两年再获奖,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吴教授分享的可能性。如今回看诺贝尔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与其简单贴上“性别歧视”的标签 (明显的反例就是居里夫人第二次被委员会青睐时,是在1911年一人独得化学奖),不如说是前文讨论所揭示的历史偶然性。
【推荐阅读】江才健 (1997) 《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57年的物理学奖可能是有史以来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前一年”标准的唯一案例。而在医学奖的历史上,相当接近符合这一标准的工作恐怕只有1922年胰岛素的发现 (图七)。我们在研究这一案例后发现,运气在胰岛素的发现过程中占据了显赫的主导地位,虽然它并没有跳出巴斯德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之范围。
胰岛素故事的“男一号”班廷医生 (Frederick Banting),于1916年从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UT) 医学院提前结业而马上参军,投身于在英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1918年在康布雷战役 (Battle of Cambrai) 中光荣负伤。从军队退役后,想以外科医生为职业的班廷诸事不顺,没能在UT著名的儿科医院谋得正式职位。为了靠近与未婚妻Edith Roach任教的高中,1920年7月,班廷选择离开从小长大的多伦多北面小镇Alliston,来到了多伦多西边110英里外的London市开了一个私人诊所。
诊所开张后可谓门可罗雀,班廷只能靠经济状况富足的父母接济才能勉强度日,而未婚妻Edith已有稳定的教师工作和相当体面的收入。1920年代,一个有自尊心的加拿大男士显然无法接受要靠妻子的收入来“吃软饭”的局面,因此班廷一再推迟婚期,又给自己增添了感情生活上的危机。为了弥补诊所生意的惨淡,班廷开始在London市的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 WU) 兼职外科学和解剖学的讲师。

图七来源: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Youtube视频:1988年加拿大影片“Glory Enough for All”,汉语配音译制版《共同的荣誉》(1991年8月24日至9月14日,中央电视台每周六晚“正大剧场”分四次播出)。
1920年10月30日,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班廷正在为主管教授米勒 (F.R. Miller) 临时给他的讲课任务而犯愁,题目是他完全不熟悉的糖代谢与糖尿病。经过几个小时“临时抱佛脚”式的教科书阅读和摘录,班廷在备课结束时随手拿起刚收到的当年11月号“Surgery,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期刊作为临睡前的催眠读物。有趣的是,本期杂志的第一篇就是美国病理学家巴伦 (Moses Barron) 讨论胰岛 (Islets of Langerhans) 与糖尿病关系的论文 (图八)。

图八:美国医生巴伦探讨胰岛和糖尿病潜在关系的论文
巴伦在研究一例罕见的胰腺结石病理切片时,发现结石阻断胰管导致的胰腺萎缩和文献中报道的实验动物胰管结扎模型颇有相似之处。事后回看,巴伦通过病理比较的推理并不严谨,并不能确立胰岛细胞与糖尿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读了论文之后依然无法入睡的班廷,当挂钟敲响星期天凌晨2点时突发奇想,匆忙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实验方案:通过结扎狗的胰管使得胰腺泡细胞 (acinar cells) 退化而外分泌减少,负责内分泌的胰岛细胞 (islet cells) 无碍。这样也许可以从萎缩的胰腺中抽提出可以用来缓解糖尿病的物质 (图九)。班廷在这里想要减少外分泌的直觉依据是,胰腺分泌的蛋白酶如果大量存在于抽提物中,很可能会破坏想要纯化的物质。


图九:班廷医生在1920年10月31日凌晨2点写下的实验设计灵感。来源: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班廷在下周一讲课完毕后,忍不住和米勒教授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神经生理学出身的米勒对糖代谢完全不了解,但他知道当时正在班廷母校多伦多大学任教的麦克劳德教授 (John Macleod) 是糖尿病领域的权威,建议班廷尽快去找他谈。班廷曾在读医学院以及当兵期间,结识了被他视为教父般的多大儿科医院第一位首席外科医生斯塔(Clarence Starr)。通过斯塔的牵线搭桥,班廷于1920年11月8日在麦克劳德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素昧平生的权威学者。
这次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麦克劳德发现眼前的这位年轻医生对糖尿病和胰腺生理学只有非常肤浅的书本知识,而且在此前没有任何实验室研究经历。麦克劳德不得不提醒班廷,此前已有很多生理学家在装备良好的实验室里耗费了很多年甚至整个职业生涯,也没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胰腺内分泌的存在。不善言辞的班廷具有执着的信念,在看到麦克劳德已把注意力转向手上其它事情后依然断断续续地不停谈他的实验构想。此时麦克劳德转念一想,反正用萎缩的动物胰腺作为实验材料确实还没人尝试过,此人既然是外科医生,结扎手术技能还是靠谱的,不如提供几条狗让他试试,就算是阴性结果也是有意义的。

图十来源:Whitford, I. et al (2012) The Einstein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28(1): 12-17.
班廷在麦克劳德初步同意提供实验条件后还有一个需要操心的问题:这份临时的全职科研工作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如果决定上马,班廷就需要暂时关闭在London市的诊所,而去多伦多进行一场个人职业生涯的豪赌!经历了4个月的思想斗争后,班廷不顾斯塔的反对,在1921年3月8日给麦克劳德写信,告知自己愿意在5月的下半月加上6月和7月来到后者提供的实验室里义务工作。
麦克劳德事先已定了1921年6月15日到9月20日去苏格兰的度假方案,在出发前有一个月的时间帮助班廷的动物实验起步。他指派了本科生贝斯特 (Charles Best) 作为班廷的实验助手,专门负责测量实验狗的血糖和尿糖。详细的实验方案如图十所示,先把健康的狗分为两大组,对其中一组实施胰腺切除手术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红色),而对另外一组实施胰管结扎手术 (灰褐色),在外分泌细胞萎缩后再把胰腺取出并纯化抽提液。随后再把胰腺已被切除的糖尿病狗分为两小组,将抽提液注射到其中一组动物的血液之中,并随时观察体征并测量血糖和尿糖。
班廷和贝斯特的实验初期出现了各种问题,导致不少实验动物的死亡。而他们的实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恐怕要感谢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动物实验管理条例还很不完善。麦克劳德在出发度假前的一个月内给出了不少具体建议,其中6月9日和14日的内容都通过班廷的笔记本档案而得以保留。
实验进行到7月初依然没有起色,那时班廷和贝斯特已经用了19条狗,其中12个属于非正常死亡,只有2个是正常死亡。存活的5条狗属于胰管结扎组,其中只有2条出现了胰腺萎缩的症状。1921年7月的多伦多之夏极其炎热,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在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奋战之辛苦。7月30日,班廷“主演的剧情”开始慢慢发生反转,他在手术时发现6月7号胰管被结扎的391号狗胰腺萎缩明显,于是断然决定对其制备抽提液。早上10:15,班廷将4毫升抽提液通过静脉注入胰腺被切除的410号狗,贝斯特测出的血糖值是0.20。一个小时后,血糖下降了40%而到了0.12,此时班廷又注射了5毫升抽提液,但一个小时后血糖只降到0.11。到了下午2:15,之前的“战果”开始消退,血糖回升到了0.14 (图十一)。到了第二天早上,410号狗还是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但两人的士气还是深受这个小进展的鼓舞,第一天观察到的40%血糖下降是个很好的兆头。

图十一来源: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8月1日是个星期一,两人接着上周六的势头继续尝试,此时他们手上只剩一条胰腺已被切除的406号狗,中午12:10时血糖高达0.50,已在昏迷状态,看上去奄奄一息。班廷将8毫升抽提液注入,一小时后血糖虽然只降到0.42,但令两人无比惊喜的是,406号狗此时站了起来并能在地上行走!下午1:10这一时刻堪比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跳出浴缸的“尤里卡”,两人兴奋地把406号狗牵到实验大楼房顶上拍照留念 (图十二)。

图十二来源: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随后班廷又注射了5毫升抽提液,到了下午2:10,血糖降到了0.30。可惜好景不长,406号狗很快又进入昏迷状态,并于3:30死亡 (图十三)。但从昏迷到站立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图十三来源: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接下来胰岛素如何被最终发现的故事就无需作者在此详述了,有兴趣者可以参阅优秀科学史学家Michael Bliss的名著《The Discovery of Insulin》。从转化医学和新药研发的视角来看,胰岛素发现过程中的诸多机缘巧合(serendipity)无疑是前无古人:(1) 糖尿病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特异性生物标记(biomarker):血糖,虽然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分析化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但检测葡萄糖浓度可以由一个本科生胜任;(2) 班廷等人发现的胰岛素是一种激素,无需任何蛋白工程的修饰,直接注射入血液可以达到疗效。相比之下,1980年代健赞公司(Genzyme)用酶替代疗法治疗多种罕见病时,必须对蛋白进行修饰才能确保注入血液后最终进入器官组织细胞内的溶酶体;(3) 几十年后有了蛋白测序技术,人们才意识到成熟的人源胰岛素序列,其A链和B链与多种动物的相应序列只差一两个氨基酸,在功能上完全可以相互替代 (图十四),而无需动用直到1970年代末才登上历史舞台的重组DNA技术。换言之,胰岛素作为一种治疗用蛋白,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应用几乎是“无缝转化” (seamless translation)。

图十四来源:labpedia.net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用在动物身上的胰腺抽提液纯度不高时问题还不大,但若要把胰腺抽提液用到糖尿病人的临床试验,对胰岛素的纯度要求就很高。而对这个蛋白的纯化攻坚,离不开1921-1922学年在麦克劳德实验室学术休假的顶尖生物化学家科利普教授 (James Collip),他的重要贡献后来被贝斯特利用“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t history) 小动作而一度淡化,直到1980年代很多第一手史料面世后才正本清源。
1922年1月11日下午,多伦多总医院的内科医生杰弗里 (Edward Jeffrey) 将15毫升由贝斯特初步纯化的狗源胰岛素抽提液注入已经病危的14岁糖尿病男孩汤普森 (Leonard Thompson) 体内。几个小时后病人的血糖和尿糖虽然都有明显下降,但是病情的总体改善有限,而且抽提液中的杂质还导致了病人的过敏反应。两周之后的1月23日上午11点,坎贝尔医生 (Walter Campbell) 给汤普森注射了5毫升由科利普纯化的抽提液,下午5点又注射了20毫升,第二天先后又注射了两次10毫升。整个疗程进行了一个多月后,医学史上首个糖尿病人的胰岛素疗法临床试验正式宣告成功 (图十五)。

图十五:第一个在多伦多总医院成功接受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人Leonard Thompson
1923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最终由班廷和麦克劳德两人分享,班廷决定把他的一半奖金与贝斯特平分,作为回应,麦克劳德把他的一半与科利普平分。这种特殊的分配方式,让根据《The Discovery of Insulin》改编的电影获得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名字:Glory Enough for All (《共同的荣誉》)。
【推荐阅读】Bliss, M. (1982)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版权声明:
-
文中图片取自网络,根据CCO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
-
本文为药时代专栏作者的原创文章,授权药时代独家首发。欢迎转发到微信群、朋友圈。谢绝转载。
-
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衷心感谢!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徐亦迅,赛诺菲制药公司转化科学部计算生物学总监。博士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先后就职于五家生物制药公司。他曾在美国默克制药公司的系统毒理学组负责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数据的整合,在代谢组学应用于小分子药物的安全性测试上取得进展。之后曾在Infinity公司从事直接与抗癌药临床试验有关的生物信息学项目。2016年加入赛诺菲以来,一直专注于各类组学数据与遗传学数据的整合,对多个自身免疫病和罕见病新药研发项目做出贡献。

发布者:药时代,转载请首先联系contact@drugtimes.cn获得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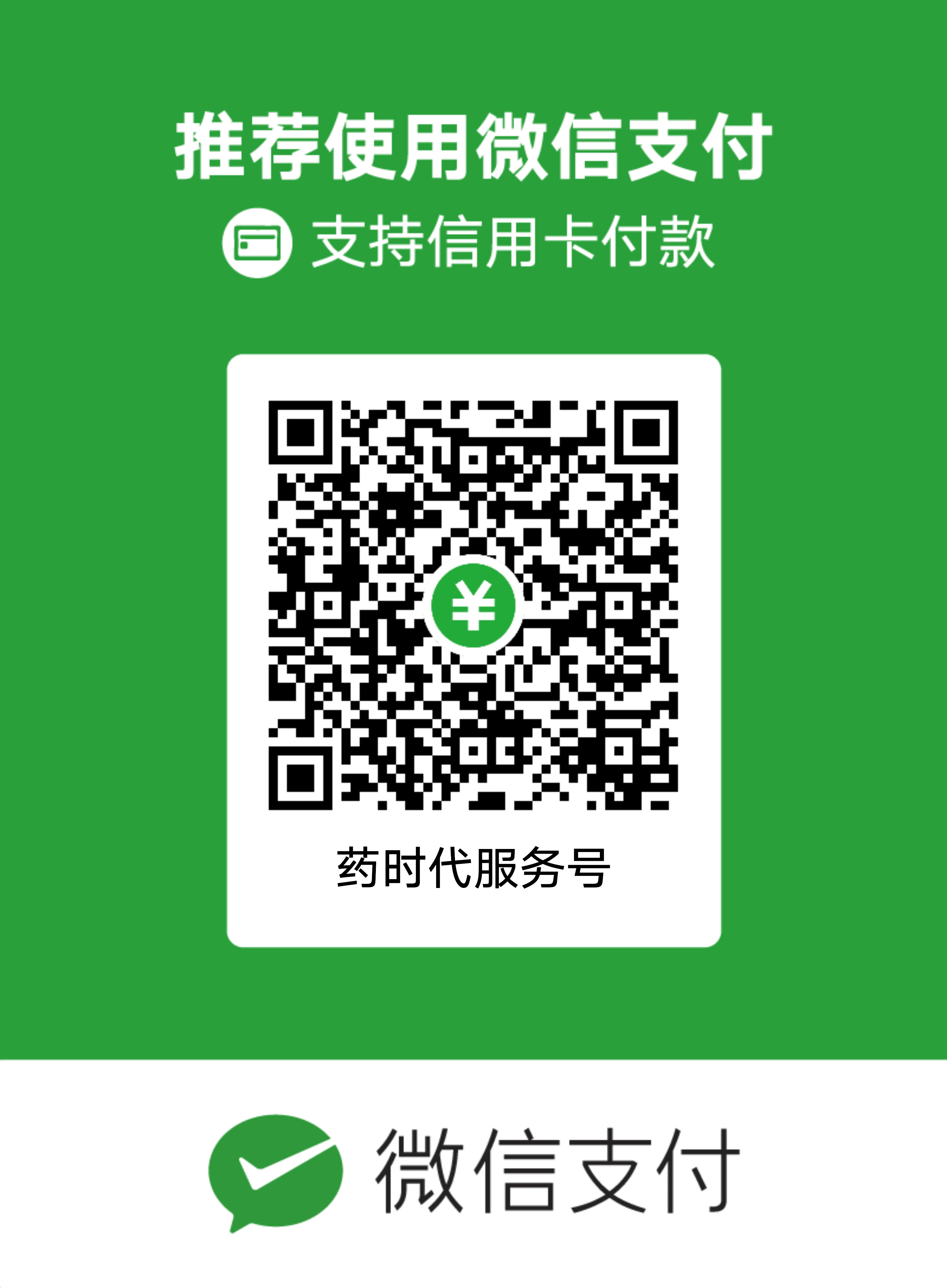 为好文打赏 支持药时代 共创新未来!
为好文打赏 支持药时代 共创新未来! 